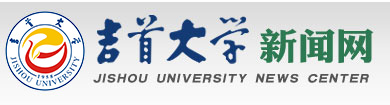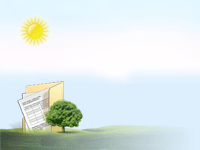最近,老是会有一种向大家推荐麻成金同志的冲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呢?或许是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周围的人渐渐缺少了老麻身上的一些珍贵的东西。
和老麻同年留校,最初又被分配在同一栋楼、同一层居住,现在的住所也挨得很近,但平常交往不多。二十多年了,偶尔在上班、下班或加班的路上碰到,我叫他一声“老麻”,他回应一声“老肖”,很少有更多的言语。然而,就是这么一句简短的回应,总能让人体会到同事的亲切与实在。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老麻有过一次单独谈话。那时,他非常严肃,甚至有些拘谨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请辞学院的领导职务。谈话的时间不太长,主要是他讲我听。他谈的完全是请辞的个人原因,没有丝毫对同事的埋怨,没有点滴对上级的不满。谈话坦诚,以致于最后我都忘记了做他在领导岗位上的挽留工作。
我和很多人一样,都知道老麻能喝酒。大家谈老麻喝酒的故事,偶尔还会带那么一点传奇色彩。前些年还能看见他用塑料壶在街上打酒。这几年,老麻患痛风,很少喝酒了。倘若见他喝酒,必定是教研室或者是工会小组打牙祭,而且多半还是老麻供酒。老麻请辞了学院领导职务,却乐意做教研室的工作,做工会的工作,并且把教研室的工作和工会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这些热闹的场面见到带有几分醉意的老麻,不由得就会产生一份敬意,尤其是他话语中夹带的点点苗语尾音,更会让人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质朴。
老麻喝酒有境界,为人处事也确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