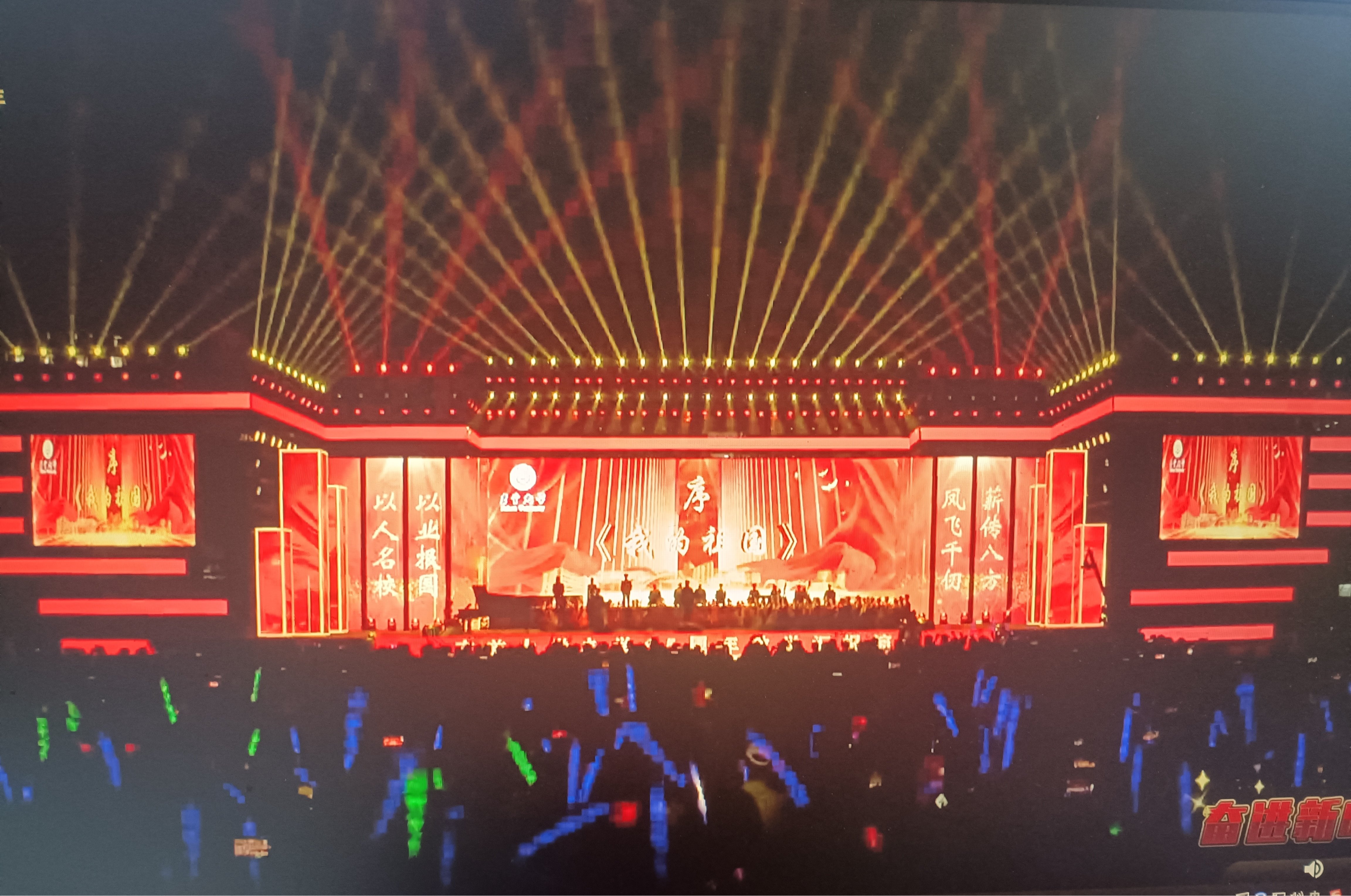由“这儿”到“那儿”
重回这园子,已是物是人非。赶上新生军训汇操和又一拨补录的新生报到。某日把我召回来。是邀请我参加建校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关于回顾,关于总结,关于已告一段落,关于久别重逢的复杂心绪,关于……
这是毕业一年零3个月后我再一次踏回这园子。虽然,我们在南北相隔的两座城;虽然从太原3个半小时飞抵长沙,再转9个小时的火车抵吉首;虽然梦里,我辗转着曾悄悄回来过很多次。说不清是怎样的情感,许是近君情“怯”,许是她在我心底已经足够熟悉,即便不去回头,不会怀念,我也知道她在哪儿,且一直在。
半旧的寝室楼在这“秋老虎”般的时节还是显得燥热难耐。我就在这样的午后挥汗如雨的四处走着,忙着在人堆儿里找寻我昔日的恩师和旧友。忙着拿手里的相机记录---假如,真的可以记下来什么。
后来,06级的师弟去总理楼的小超市给我买了一瓶带冰的百事,当冰爽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落到胸口震得一秒闷痛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我想起之前很多个夏天,和好友一起从演播室上完课出来时总是要买两罐带冰的百事,然后一口气猛灌一大口,为的其实就是那一股暗爽的疼痛。
你说,你们的故事总是这样,由此及彼,有分外清晰到模糊淡出,那时候我们还坐在空旷的10楼演播室里看一段闷闷的纪录片,那时候我们以为所有的眼前的都不会消散。
直到某一天,我又重新回这园子,看别人的大学生活,才发现原来属于自己的时光真的已潜渡成由“这儿”到“那儿”的距离。
致体育馆大门
经常用于进出的是体育馆的校门,因为距离宿舍近、乘车去市区方便、可以逛小商品店、有很多家食品店或小吃摊,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理由,就是路遇体育场看见的帅哥很多,但大多有女友。虽然如此,最被认同的仍是面向一个很个性的花坛的正门——东大门。
进门即是漆金大字的石碑,上书“吉首大学”六字,落款从没有在意过,但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名字,却是因你牢牢的在心底扎下根。记忆中,似乎在我刚进校时,校名那几个字还有些小,具体何时改大翻新了,印象也很模糊了。
致宿舍楼
番号是4,和老校区的6栋女生公寓比起来,很让人心生不平之感,尤其当住宿费一般无二的时候。每一间窄窄地放下三张双层床,另侧是书桌和吊柜,放被褥时需要动用一架铁梯,四年下来,我们都搬运迅速、攀爬自如。
你直白地露着灰白基调的水泥材质伫立在那里,宿舍里也甚是荒凉,除了两盏日光灯,没有其它任何电器,甚至连风扇都没有。打破我对于大学的第一个,有关现代和时尚的幻想,懒得理会我的生气。
你静静任男生们骑着自行车在你面前的空地绕着圈等待女生们,任熄灯前男生女生们三两成对聚在你楼前的阴影中说话。熄灯后,有人打灯看书有人哭,有人溜进已经半关的卷帘门跑上空荡的楼梯回宿舍,留下外面的男生醉倒在你的花坛边。
你什么也不回应,四年一过你就把我们都清空忘记。
而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准确地想起你离前面的女生宿舍与后面的男生宿舍的距离,篮球场上干燥的尘土气……和站在你的门口绝对看不见,却总在我的记忆里泛着闪闪粼光的,你右侧50米之外,贯穿校园的那眼大大的湖。
致电话卡
你一副没有什么收集价值的长相,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大摞。
下铺的舍友应该最多吧,她大学前两年是异地恋,和她的高中同学小男朋友每天电话粥煲个三四小时是常事,也欢笑,也痛哭,也吵架,也撒娇。
通过你,有传达出或传达进很多青涩而纯真的青春的情感,但重点不是这样的事情。
重点是四年不断增加的电话卡数目,是同宿舍女孩生病后拿起你给妈妈打电话大哭一场……
是你给困在宿舍、班级、林荫路、非编机房、演播室中,不小心越来越偏执坚硬的我们,那么多变得柔软的力量。
致主楼
教学区牌号第一的楼,其实是文学院的楼,和后来新建起来的“总理楼”比,甚至和对过的资环、化工的楼、商学院的“布达拉宫”比,真的很旧,但这里才是这所大学最核心的所在。花白头发的教授、柔和静美的女生,都显示了一种积淀的沧桑,是品味内涵的精髓。
四年大学的文化课程的学习,除了英语听力、大三的专业选修课,都在这座楼里进行。
可是,当时我们是那样的轻狂和浮躁,我们常常翘课、代点名、迟到、早退。
最变态的一个外系基础课老师,曾想出每节课换着样的在课前、课中、课后的点名,并且一学期被点到三次,期末成绩一律不及格的损招。偏偏他的课,枯燥无味,颇为饶舌,而且连上三节,让人如坐针毡、分外难熬。
但我还是早退了一次,并没有被抓到。
我和同伴那天早晨手拉着手,趁着第二节下课从后门跑掉,把你甩在背后越来越远,带着逃课带来的空虚的骄傲。
致图书馆
有四层,常去的是负一层的文科书库和二层的新闻传媒阅览室,也在学习区攻书,也在休息室泡咖啡、和朋友聊天。收到过一些小纸条,也有真的认识一两个很好的男孩子,只是那时侯的我,对于爱情,是那样的抵触和固执。
那些男孩子的名字,我忘记了,你还记得吗?
致演奏厅
不记得了,或者,是真的数不明白了。
很多次,我留恋你这里的那方舞台,留恋我头顶上方不熄的灯火,留恋手上捏着的麦克风。
这里,不仅仅满足着年纪轻轻的我那颗有些虚荣的心。
这里,也同样承载着我年少以来一直珍藏的信仰。
这方被这园子里的人们誉为“最高”的舞台,看着我走来,看着我成长,看着我从台前到幕后,看着我带出来一拨一拨的主持人,尔后,看着我走了又回来,回来又离开。
致每年一度的校运动会
对不起,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像个高中生一样,每次都想尽办法逃脱掉,是为什么呢?
致自习室
迷惘、茫然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很多当初我们执着过的念念不忘的梦想,输给了苍凉的时间、奋斗无门的窘境,以及对于太过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
我们从没有好好上过几次自习,经常找不到位置就放弃,或趴在占好的位置上睡觉。
你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不爱学习,除了上课时间都不来见你的学生的?你可能都懒得批评我们的幼稚和不清醒,随着我们去挥霍青春,随我们用几年时间慢慢沉淀,越来越怀念你。
你赢了。
今时今日,我坐在自己的家中,在电脑前码字。这里灯光充足,设施完备,窗户的玻璃边框没有一丝灰尘。这里,一点也不像你。
但是,只要我坐在书桌边静静地看书、做题、码字时,时常会陷进错觉。以为自己坐在你半旧的教室里,墙边装着暖气管子,窗台总有擦不干净的灰尘。半个小时后我将下课,随同学回寝室。
我不停被你当年默默构筑的影像侵袭,时至今日。
致我的大学
大一刚刚进校报到的我,全家陪同,甚是隆重。随着襄樊至湛江的那一班绿皮车超慢的时速,在隧道与隧道之间穿梭,没有片点的信号,一公里一公里地朝你开去。列车到达,我觉得自己似乎空空如也——对于过去的丧失和对于未来的无从把握。这个布满陌生人和灰白色建筑的校园,以及就读的听起来很热门又拉风的专业,能否在四年的光景里,把我变成另一个想要的自己。
结果当然没有这么美好。我甚至从开始就对一切很生气。经济落后的湘西、荒凉的宿舍、只有名字拉风的专业、让人失望的城市治安……沉闷压抑的高校。
所以四年以来,我一直以一种轻视、疏离的姿态,拒绝和她的亲近,无时无刻不思忖着匆匆逃跑。我气愤、焦急、无奈、空空如也……我甚至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下“上这所大学是我今生不能排遣的忧伤和郁结,我在试图脱离,拼尽全力,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飞离这个幽杀一切的古墓来赢得新生。这需要勇气、坚持、抗争、沉静……这些我原本都不具备的东西,我在培养,在忍耐。”这样决绝的句子。
我该怎样和你说起自己?你一定不记得我。你也有不少知名的校友,他们功成名就。你完全不必记得像我这样一个不擅学习、有些白白浪费了你,都拿着省特优毕业生证书,却无缘校优秀毕业生典礼的某届毕业生。
虽然,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对你还是有蛮深厚的感情。
最近看到的关于你的照片,是在学校主页上的图片。风雨湖、玉虹桥、齐鲁大楼、布达拉,以及一树开得艳丽饱满的玉兰花。
即使曾经多么不耐烦、不满、不屑,急于逃离。即使毕业后从未回去看一眼的我,现在对于你,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即使每次别人问起,我还是嘴硬地反复调侃那个古旧且又似乎与些许“丑陋”的第一教学楼;耗费巨资修建我们在时却似乎还使用率奇低的齐鲁大楼;以及公寓的马路被称为“堕落一条街”这些事情。但是——
但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些轻佻调侃里的温柔记忆,是怎么样在这许多年间,不间断地、一点一点地扑满从你那里毕业的每一个人的心和身体。
我在你那里,走过了自己最好的时光,如今依然,心甘情愿被埋进你几十万分之一里,作为不必被提起名字的成员之一。
(作者徐越,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3级校友,现供职于山西传媒学院,央视环保频道主持人)

图为徐越(左二)回母校时与文学院原党总支书记张和宇(左三)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