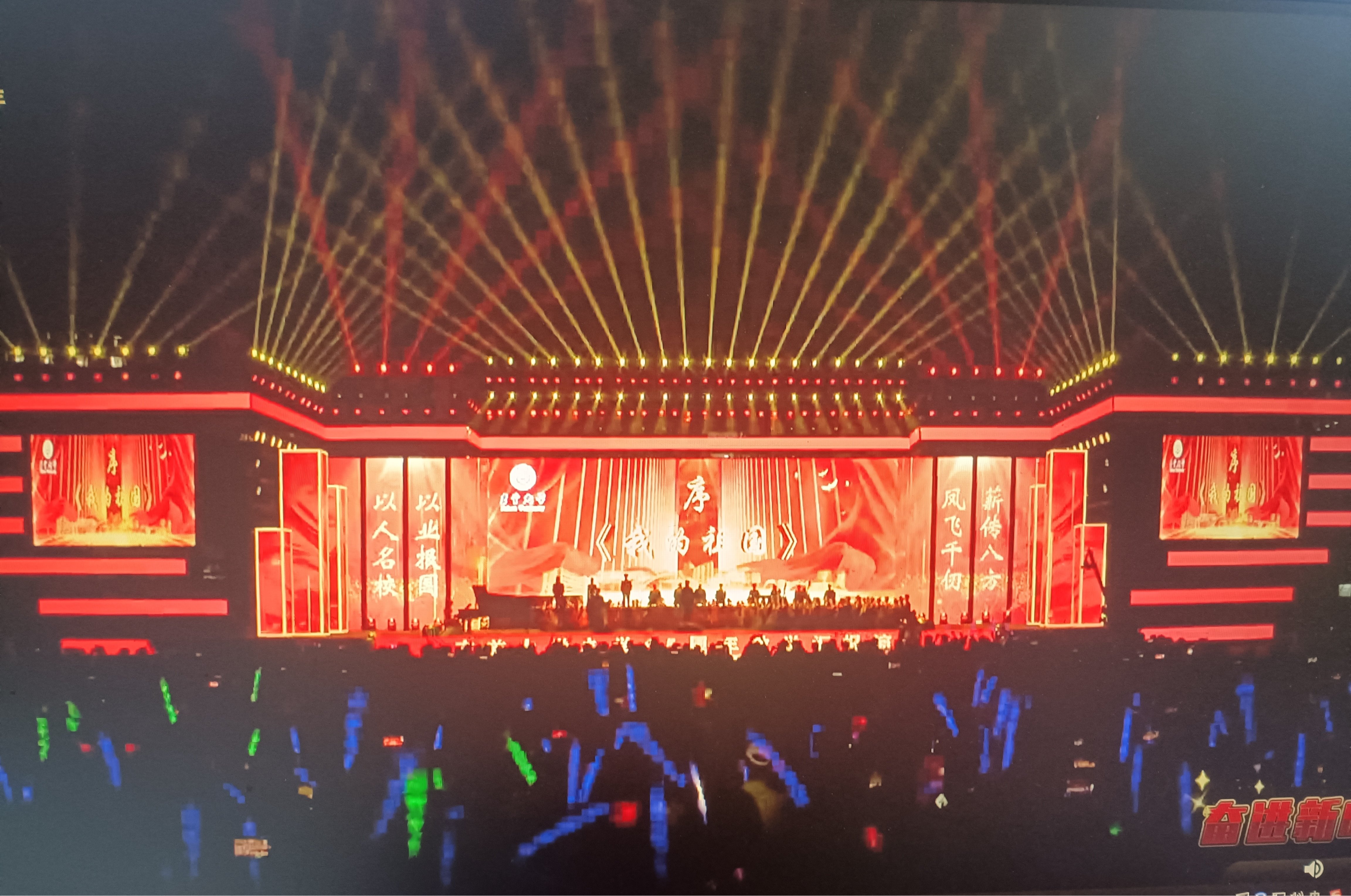福修福报,徳修德报。
母爱如山,母爱如天。
我生在大山里头,地理上属雪峰山脉,行政地名过去叫长丰乡曙光村,现在叫天门乡树溪村,乡名管她叫天门也好,长丰也好,总觉得村名还是叫曙光村大气。站在天界或峰顶,看到的应只是曙光、太阳、月亮、星星,顺理成章。也许地质年代,沧海桑田,曙光村中间一条常年不断的河流,两面大山深情对视,形成一个巨大的“V”字,“V”——西方人意为“胜利”“成功”。乃祥福之地。村里大大小小自然寨好几十个,每个寨名都充满了皇家气息。我家附近就有曾家坡、邓家坪、陈家屋场、张家溏 、孟公洞、金家溪 ……屋后是天府坪。链接上下五千年,都能顺上龙脉,寻到源头。我家住的小地名叫方碑基,那是清朝咸丰年间朝廷颁立的一块礼碑,碑铭大意是这样昭示路人的“公务私差,路过此地,不得骑马坐轿,只能步行通过。”从巨型底座到高大碑身,四四方方,方碑基由此得名。相传,此地风水龙脉好,出高官显贵的地方。这里虽然很山,乡亲邻里很斯文地管自己的娘都叫妈妈。
我儿时记忆中的妈妈一脸艰辛与慈祥。邓家坪小学离家只有2里多路。大概4、5岁的那个样子,我跟妈妈说,家里我最小,不好玩,我要去读书。正在煮饭的妈妈转身看了我一眼,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锅墨和汗水,从裤兜里掏出卷着的小手绢,拿出二元五毛钱,摘下墙上那个黄里发白的“为人民服务”的包包,让我去了学校。70年代前后出生的山里孩子,多少是要吃些玉米、红薯才长得大。物质短缺年代,一锅饭半锅薯米。我有一次放学回家,打猪草时候被野蜂蛰了眉宇一针,两个眼睛都肿得像桃子,怎么睁也睁不开。村里乡亲说了个古传偏方——奶水可治。妈妈好不容易挤出了几滴奶水涂在我眼皮红肿处。吃晚饭时,特地在饭上做了一个水蒸蛋,扒开一层又一层薯米找到了一碗白米饭给我吃。看得出,妈妈很心疼我。
哥姐们心中的妈妈勤劳而勇武。妈妈拉扯大我们8个,不简单。现代人特别是西方人谈“育”变色,望而生畏。哥哥姐姐告诉我,大集体时代是要出工、记工分的,靠工分吃饭。早上天未亮,就要上山“打锣鼓”。晚上,月亮出来好久了,才收工,兄姐们和我,柴房里、门角落、门槛下,哪里困了就在哪里入梦。妈妈有时顾不上吃饭洗脚,倒头就睡。爸爸是土改干部,是全省第一批共产党员,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会写会算,算个知识分子,在外面工作。妈妈不识字,带孩子、出集体工。村里有人说,女同志只记6分工,不能分平均口粮。平日里最讲理的妈妈这时也有点生气了,在村部挑着一担一、二百斤玉米的箩筐,扁担两头一拉,舞了一路心惊肉跳的祖传长棍,村里记10分工的甲等劳动力都目瞪口呆,都变了,异口同声讲:何婶娘天天和我们做一样的工,出一样的汗,当然要记甲等工。
乡亲们口中的妈妈贤德又友善。逢年过节,我爸爸总要忆苦思甜。他说过,很小时,春节前后雪天穿草鞋送财神菩萨,近到琅瑭、白溪、孟公桥,远到双林江、奉家山、桥江、江东。说白了,就和讨米差不多。爸妈从苦边来,懂得生活的艰辛,从不忘本,见了乡亲缺衣少食,二话不说尽其所有去接济。自己家有肉吃,邻居都有份。春节前后,上门讨米的来了,大碗装肉装饭,还要打发肉和糍粑。遇到五黄三月,自己少吃一碗饭,都要把叫花子的碗填满。有一次,妈妈给小姐姐过生日煮的两只干鸡腿,把我心里馋了很久的一只鸡腿都分了给讨米的吃。
老师同学眼中的妈妈重教明理。哥姐读书时,我还小。哥姐挨妈妈的打,都是为读书的事。那时候,哥哥姐姐又要读书,又要放牛做农活,有时索性旷课在家干活。妈妈急了,见状拿了竹条子抽他们,赶他们去二十多里山路以外的长丰中学读书。我读书时,三年级以后也要走十五里山路到高田村的横板桥小学。天还未亮,妈妈起来给我做油炒饭,妈妈说,中午学校没饭吃,很晚才回家能吃饭,油炒饭经得起饿。读小学,我个子小,去学校要过五道河,蹒跚漫过溪河,记得有好几次被洪水冲走了,双手仍紧紧抱着书包,连续翻滚,后来被树挂住了。我每次对妈妈说起被洪水冲走的故事,妈妈始终鼓励我莫言退,要勇进。初中毕业时,我好像是全乡第一个考上了全省重点中学——新化一中,一中名气大,陈天华、龚谷城……都是一中的学生。在一中读书时,有一天早自习,爸爸妈妈到教室来看我。妈妈和退了休的爸爸专门从老家杀了一只鸡蒸熟,提了一些鸡蛋,步行几十公里山路,乘汽车、转火车。爸爸拄着拐杖,带着伴他一生的眼镜。父愿子成龙,可怜天下父母心。记得在校门口临别时,爸妈的眼神里,充满自豪,又饱含期待。
我的妈妈今年88岁了,比爸爸小15岁,要是爸爸还健在,也是百岁老人了。大学毕业后,我妈妈在湘西和我生活了11年,75岁时硬要回曙光住,她舍不得那里的乡亲、山水、还有那菜园土。我妈妈每天都扛着锄头去一次菜地,锄锄草,摘摘菜,上山割割草、打打柴。精神还好,头发并未全白,思维敏捷。勤劳、善良是她永远不变的习惯。
(本文作者系湘西州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