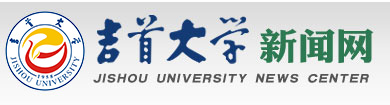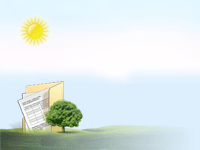秋风渐吹渐紧的时候,娘背上篓子,钻进棉花地里,一溜烟就没了影子。跟在她身后的我,被甩出几十米远。我的家乡常闹秋旱,龟裂的土地像干瘪的乌唇,碰着燥燥的。叶子拉耸着脑袋,炸蕾的棉花吐着发白的舌头,一条一条密密的挂着,像老头子的山羊胡。
“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个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我一边唱着歌谣,一边摘着即将与我肌肤相亲的棉花。娘站在日头下,笑容明晃晃的,四角棉花从背篓里掉出来,像挣脱篓子的蝴蝶。
回家后,娘拖出新摘的几麻袋棉花倒在门前的空地上,胖头胖脑的棉花一股脑儿溜了出来,咧开嘴笑着闹着。娘用竹耙把它们推散,她系着宽大的围裙蹲在棉花堆里,爱抚地托着棉花,轻轻掸去上面的灰尘,像在收拾她水灵灵的闺女。娘把拣好的棉花丢进裙兜里,像怀揣着一个嫩娃娃。雪白的棉花儿在阳光下亮亮的,娘的汗珠也亮亮的。
娘把挑好的棉花送到村口弹花匞家里去籽。弹花匞有条不紊的弹花、铺絮、拉线、碾棉胎,弹飞的棉絮糊满了屋瓦,远看那黝黑的土培房像一棵高大的桐花树。
卖棉花这天,娘把仓库里的板车拖出来,那是辆用了好些年头的板车,有的地方已经腐烂,布满霉点,像密密麻麻的老年斑。娘打了桶水,顺着老板车的胳膊奋力地擦着,弄掉了好些木条儿。随后娘和爹抡起一袋袋棉花往板车屁股上丢,爹把棉花口袋摆在板车上,把板车的胳膊、肚子、大腿都牢牢实实捆起来,一切收拾水灵后,就准备出发了。爹双手架在板车杆子上,走在前面拖着板车。娘扶着口袋跟在后面,经过土坡时,娘 “嘿哧嘿哧”的喘着粗气,卯足了劲推车来帮爹省力。走到镇上的棉花站大概要几十分钟,爹和娘就这样一前一后,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趟。我等在坝梗上,麻雀从田里钻出来又飞过去,远远地看着娘哼着小调和爹踏着夕阳回来。
堂屋的棉花空了,娘的荷包胀鼓鼓的。赶集前,娘用手巾把钱里外裹了好几层,塞进大白衫的内侧口袋,就背着我出发了。天还没亮,田埂上黑蒙蒙的一片,娘背着我走了好长一段路,身上桂花油的香味在我的鼻尖荡来荡去。我再睁眼时,阳光已经洒满娘的发了。
集市上人很多,娘紧紧地牵着我,不准我离开她的视线半步。每次上街,娘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买吃的。她的篮子里装着一袋子米花糖,我跟在娘后面,把酸甜的糖葫芦塞进嘴巴里,秋的气息便透过皓齿落到了心上。
娘在挂满花花绿绿布条儿的铺子前停下来,她左手捏捏灰缎子,右手攥着一块红布,眼睛又盯上了铺子中央的那块碎花布。旁边有几个妇女涨红了脸,操着一口浓厚的乡音和老板杀价周旋,一会儿把桌上的那块布拿起来挑三拣四,一会儿又嫌弃似的丢回去,那阵势果真像戏台上横眉竖眼的大母虫。娘是从来不杀价的,她在一堆布里来回挑捡,偶尔低头问问我的意见,等心中拿定了主意才喊来老板。“给孩子裁三尺布。”娘说。回来时,我一路上欢喜地抱着那新缎子,一会儿把头埋进去,一会儿搭在身上,扮那漂亮的新嫁娘。娘老远跟在我后面,她洗的素白的衣衫在秋风里飘荡。
布买回家了,我天天盼着娘给我做袄子穿。娘看着外面的天,总说:“等等吧!棉花再晒几天就能装衣服里啦!”一个傍晚,娘从地里回来,鞋子上糊满了新泥,身上还带着苞谷的清香。她把铺满棉花的大筛子搬回堂屋里,又把缝纫机擦了好几遍,终于答应今晚就帮我做棉袄。吃过晚饭,娘不紧不慢地收拾着碗筷,然后去笼子里侍候着鸡鸭,花布还挂在晾衣杆子上,像一只手挠得我心里直痒痒。
夜深了,娘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里摇曳。我蹲在缝纫机旁,紧紧盯着娘。娘拿着大剪刀麻利地扯下一截布来,放在案上,右脚踩着缝纫机的脚柄,针头“哒哒哒”的缝着衣口,像缝着紧紧凑凑的日子。我揉着疲倦的睡眼,模糊中看见了好几个娘都在眯着眼睛对准衣服的边线。不知道睡了多久,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躺在床上。门掩着,娘早已下地干活去了。
娘连续做了几个晚上的缝纫活儿,棉衣终于做好了。是件蓝底红花的棉袄,两侧特意缝了很深的口袋,一排水灵灵的扣子闪闪发亮。娘说这种“种子棉”经水以后穿就不暖和了,所以棉袄是不常洗的,一穿就是一个冬天。娘清楚我爱弄脏衣服,于是她把剩下的碎布拼在一起给我缝了双小护袖,套在衣口处。
高考那年,我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大学,而家里的条件难以支撑我重头再来。那一年的暑假,雨水特别多,我整天闷闷不乐,把自己关在家中不愿走动。去学校报到的前几天,天气突然放晴了,阳光好的出奇。那个时候娘的眼睛已经变坏了,不能再给我做棉袄穿,她把床底的木箱子拖出来,在底层挑出来几件还算新的棉袄晒在外面的架子上。阳光下,娘一边拍打着棉袄一边自言自语:“过日子啊,就像穿棉袄,有湿气了多拿出来晒晒,穿着就暖和了。”我收拾着东西,默默地听着。第二天,我拎着胀鼓鼓的行李箱,就像拎着一箱子满满的阳光。
这是我在外省过的第二个冬天。湖南气候特别潮湿,冬天的衣服拿出来都是冰凉的,穿来穿去还是娘做的棉袄穿着暖和。我把娘做的棉袄裹在身上,显得有点笨重却浑身热热乎乎的,远看像一个会走路的红薯。娘总是在傍晚从地里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每次第一句话就是让我常把被子和衣服拿出去晒。我没忍心告诉她这边雨水充沛,天晴的日子少的可怜。
娘乐不思疲的忙活了大半辈子,她总是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小调。娘的一生有两个太阳。一个太阳挂在天上,升了,娘下地干活;烈了,娘把家里的物件拆、洗、晒;落了,娘赶回家做饭、打扫。另一个太阳是我,白天,娘把爱编织成霞云,围绕在我周围。夜晚,娘不眠不休的为我赶制棉袄。她一边将蓬蓬的棉花塞进衣服里,一边将满满的幸福塞进日子里。那不断落下的针头像一个个韵脚,谱成愉悦的歌儿。娘像追日的夸父,一生都朝着她的太阳奔波。
前阵子,我在一本介绍植物的书上看到了棉花的花语是珍惜眼前的幸福,不知道怎么,我想起了娘。
(此文荣获第三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责任编辑:苏卫平 投稿邮箱:jsune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