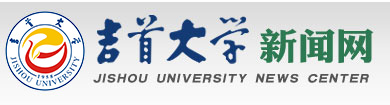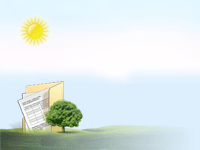住在洞庭湖湖,房前屋后有条河,是最平常的事。
洞庭湖西边有个太白湖,太白湖有个凤尾洲。我家就住凤尾洲洲头的河提上,门前就是一条河。
湖乡河太多,大多未命名。
我家门前的河也没有名字。一记事起,就慢慢知道,从家门口开船,往东可以到赵家河,往西可以到小港,到坡头;往南可以到牛角尖;经过毛家堡或易家嘴往北可以到酉港。酉港是我们公社的机关所在地,乡里人十分向往的地方。船去这些地方,近的,半天、一天来回,远的则要两天才能回家。乡里人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若是去小港、坡头,他们会盘算好时间,天不亮开船,带一钵饭菜上船,半夜三更也要赶回来。
之所以只能到这些地方,是因为解放后围湖造田,太白湖被围在西湖大垸之中。东西南北的河道都被大堤堵住了。
父辈们一直以西湖大垸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而骄傲。那时候,洞庭湖每年发大水,队里的老老少少对悬在头顶的洪水惶恐不安。
这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安慰大家:
国家是不会让西湖大垸溃堤的。
西湖大垸溃了,国家的粮食怎么办?
大家信了,安心上床睡觉。洞庭湖的洪水有国家管着,自然不会浇到自己的头顶上。
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那时候,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人如此,孩子亦如此;干部的如此,底层农民亦如此。二我家门前的河,是洞庭湖的古河道。围建西湖大垸之前,由沅水下来的船只和木排,经由这条河道,可以下长沙,去汉口,甚至去更远的地方。人们沿河筑堤,倚堤而居,是千百年来,湖区人与水搏斗、与水为伴的生存智慧。
那时候,我们都住在河提上。我们队是凤鸣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三队东头是一队和二队。一队和凤南大队的一队挨着,结合部是凤南学校。我在那里从小学读到高中。三队西头是四队。四队和五队的结合部是大队的电排站。电排站的河对岸是毛家铺。毛家铺属于文蔚公社。四队和五队随河道向右转弯转,到六队、七队,刚好位于我们队背后。加上八队、九队,整个大队形成了一个包围几千亩农田的大半圆,大概是半个凤尾洲。一堤上千口,就围着这半洲的农田繁衍生息。
我们住在河的北岸,南岸是鸭子港公社的太丰大队与风林大队结合部。东岸是本公社的晨阳大队,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沙滩。沙滩叫撂荒坪。风林大队与晨阳大队也隔着一条河,就是从那条河去牛角尖。因为坐拥三叉河道的格局,队上也就有了一个带给孩子们更多欢乐的渡船码头。三我家原本是紧挨着渡船码头住的。过德元叔家,就下渡船码头。就因为大队部要从位于东头一二队结合部的加工厂内搬出来新建,大队干部又看上了我家和德元叔家的屋场,于是,我们两家便往河堤西头搬家,离渡船码头远了十来户人家。搬家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学。现在对老屋场的记忆早已零零碎碎,模模糊糊。
只记得,我家的茅屋很小,屋前禾场(坪场)很大。小时候,在禾场上帮大人嗮柴火,摇烟包(稻草把子,湖乡主要烧柴)……小小年纪,摇烟包手特别容易酸痛,烟包车儿(chaer)不时反转,掉到地上,把手打得很痛。午后,太阳底下摇烟包还特别容易打瞌睡。
只记得,屋前屋后的鸟儿特别多。每家屋后的大树上都有喜鹊窝。每家屋前的禾场上空都有燕子飞过。热天的夜晚,禾场乘凉的人特别多,大家一起吃菜瓜特别解渴,躺在竹床上看星星特别亮。
只记得,冷天的北风特别大,特别冷,呜呜作响,刮断枯枝,钻进茅屋,钻进棉衣,把手脚和耳朵冻起冻包。
只记得,我们家是地主,奶奶是“五类”分子。经常有干部模样的人到家里和奶奶问话。奶奶总是回答过去有三十六亩湖田,两间半茅屋……干部模样的人走了,奶奶就会一人哭半天。奶奶的哭声不大,偷偷地,像说话,也像唱歌。后来,姑姑出嫁,奶奶也这么哭。一通晚,把家里人和来的亲戚哭得落泪。长大后,在奶奶幽怨的哭声里,我才真正理解“哭诉”的含义。那一刻,我也想哭。
奶奶是个苦命的人。虽然出生在常德城里的大户人家,享受过父母还有大娘、二娘的呵护,享受过专属奶妈和丫环的照料,但幼年丧母,家道败落,很小就过着流颠沛流离的生活。解放前夕,她和爷爷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钱卖得三十多亩水田,没想到,解放后确因此划为地主。爷爷在姑姑出生七天时突然病逝。拉扯刚到上学年纪的父亲和刚出生的姑姑,背着“地主分子”的身份,孤儿寡母,奶奶就这么一路艰难前行。谁能想象,奶奶的哭声里,饱含了多少冤屈呢?
……
脑海中,很少留存老屋场下河戏水或渡船码头划船的记忆。水,主凶,大人一般不让小孩下河戏水。渡船老板也会把想要尝试划船的小家伙骂得狗血淋头,灰溜溜地逃去。现存的“河”的记忆,几乎都是搬到新家后留下的。印象中,搬家不久,我就上学了。那时,我笑国家(黄国家,启蒙同学),把“2”写趴下了。这件事,记得就是他走过十来户人家,找我做作业时发生的。住老屋场时,国家的屋就在隔壁东头,坐东朝西,三间板壁青瓦正屋连半间茅草偏屋。偏屋是他外婆单独住的。那时,他外婆已是七老八十的年纪,行动迟缓,头部轻微摇摆。她会画水、“收吓”(he,“收吓”即招魂),诊“包耳风”(腮腺炎)。一堤孩子,谁吓着发烧,谁脸颊红肿得了“包儿风”,大人都会带到他外婆屋里,请他外婆画水诊治。画水诊治不收钱,据说这是祖师爷传下的规矩。带孩子离开时,大人便会从口袋里摸出两三个鸡蛋,悄悄放在灶台上。不是诊金,算是表达谢意。国家小名叫幺妹,很得他外婆的偏爱。每天天黑睡觉时,他外婆总会拄着拐杖,站在那半间茅屋的门口为他喊魂。
“幺妹儿……回来歇呀….”
“幺妹儿……回来歇呀….”
乡村的夜晚,那悠长的喊声传得特别远,一堤的人都能听到。那悠长的喊声,现在感觉还是那么清晰…..
搬到新屋,虽然不及渡船码头住得热闹,但却有了更多下河的机会。新屋建在堤上,禾场很小,嗮一挑稻草就跨界。出禾场由挑水码头下河,因为是陡坎,又没有河滩,不要一分钟就下到水桥。于是,洗衣、洗菜,甚至洗脸刷牙,都到河边。小孩腿快,我几乎包了洗菜的活。有时候,洗菜引发尿急,解开裤子便朝河面撒尿,一道抛物线便在平静的河面上击起一串串水泡。临了,还会找寻小瓦片,在河面上打起水漂……这时,大人的叫骂声也就到了。只得红着脸,乖乖地一溜小跑上堤进屋。五新屋正对南岸太丰一队的伯伯家。伯伯家宏,和父亲是堂兄弟。伯伯有一对儿女,儿子叫廷春,我叫春哥,女儿叫冬秀,我叫冬姐。母亲做媒,春哥娶了我远房舅舅家的表姐。亲上加亲,我们两家一度走得很近。后来,因为他们家婆媳矛盾长久不断,战火蔓延到我家,导致母亲和伯母关系紧张。
不过,我和春哥的关系一直很好。春哥好玩,农活不里手,就是特别喜欢打鱼捞虾。他家里,渔具齐全,有手网、干网,有渔叉、渔钩,还有浅水捉鱼的大小麻罩和专捕鲑鱼的若干花篮……春哥只比父亲小几岁,经常缠着父亲学唱老戏,学打“点子”。有事无事,他便划船过来,要么找父亲学这学那,要么在河里捕鱼捞虾,要么去屋后的田沟里捉黄鳝泥鳅。捕鱼捞虾,他偶尔会邀我作伴,让我给他打下手。
不知什么时候,他居然置办了一条专门用于夜晚捕鱼的片船。
片船,子弹剖面形状,窄而长,长度超过渡船,宽度却比渡船窄三分之一。船头很尖,头舱只容得下春哥一只脚。船尾装半圆乌棚,勉强供一人半躺挡风避雨。
划片船夜晚捕鱼,全靠一张比船体略宽,比船身略短的鱼形白色薄板。捕鱼时,白板从靠河岸的一侧下水,侧立水中与船绑定。划船前行,水中白板则如一条向前游动的巨鱼。水里受惊的鱼儿便跃起逃命,刚好落入船舱。船的另一侧必须安装拦网。当然,要有好的渔获,得熟悉河道,了解鱼情,懂得下板时机,灵活掌控片船行进的方向和速度。
也就是这条片船,差点让我和春哥葬身河底。
那是初夏的一个夜晚。
傍晚时分,春哥将片船从对岸划过来,说今晚可能是捕鱼的好天气,让我陪他出船捕鱼。夜深,春哥和我提一盏马灯下河上船。上片船得很小心。两人上船必须一人先下水把船稳住,待先上船的人在船尾坐定,后面的人再慢慢轻身上船落座。
灭了马灯,船离岸西行。我模模糊糊半躺睡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沉闷的声响将我砸醒。睁眼看船舱,好大一条翘鱼在噼噼啪啪地挣扎,片船中间的船舱舱底,也因躺满了大大小小的鱼儿变成白色。
船静悄悄地前行,进入一大片河柳底下。树阴里,几乎没有光亮,阴森恐怖。好在不时有鱼儿跃进船舱,噼噼啪啪的声音和黑暗中的一缕缕白光,冲淡了恐怖气氛。此时,我才真正明白,春哥为什么让我作伴。
出了树阴,噼噼啪啪的声音就渐渐地停息了。我问春哥到了哪里。他告诉我,已经到了杨柳。原来,我睡去之后,片船在毛家堡北拐,深入了十来里水路。
后半夜,云层里透出朦胧月光。寻得一处浅滩,春哥卸了白板和拦网,片船掉头折返。回程无需捕鱼,春哥便呵欠连天。于是,他和我交换位置。他睡觉,我划船。
鸡叫二遍,船返回到家门口时,天又莫名其妙地黑下来。叫醒春哥,我俩再次交换位置。本以为就要收船回家,不料他又寻得浅滩,重新装上白板和拦网。
我知道,他还想在天亮前捞一票。
片船又进入一带树阴,船舱里又响起噼噼啪啪的声音,只是声音细小稀疏。经过家门口,片船继续向东,一会儿便到渡船码头。此时,片船转向东南,船头指向晨阳方向。我明白过来,春哥还想去晨阳的那条河道里碰碰运气。
谁曾想,船刚到河心,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接着便是惊雷滚滚,狂风暴雨。我头顶半圆乌棚瞬间飞向天空。河面上,一下泛起大片大片的白鹅浪头。
春哥连声“拐打、拐打,莫动、莫动……”
“拐打”是家乡土话,“不好”的意思。
春哥话没说完,浪头打来,船舱满水,我俩瞬间没在水里。没有其他动作,只能各自死死抓住船舷,双腿下蹲,双脚紧叮船侧,拼命稳住身体不被浪头卷走。
开始,风暴朝东,船在水中起伏。转来转去,我们飘向晨阳方向。一阵暴雨过后,风暴方向突变,刮向西南。眼看要被卷到撂荒坪河滩的片船,又快速回飘,切河心,涌向西南太丰方向……也不知过了多久,风停了,雨歇了,天也亮了。我和春哥筋疲力尽,连同片船一起,被风浪抛到南岸的河滩上。
拦网没了,桡没了,马灯没了,船舱里的鱼儿也全没了。只是白板还在,已经支离破碎地铺在片船一侧。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那块白板帮我俩逃过生死一劫。白板绑在水下,才使得满水的船没有被浪头掀翻。也得感谢最先刮到的狂风,若不是它首先卷走半圆乌棚,也许接下来一定是船翻人落水。那种狂风巨浪之下,落水者水性再好,恐怕也难逃一死。
只是,我可怜的春哥终究命薄,三十六岁那道生命之坎没能夸过,死于肠梗阻。
(责任编辑:苏卫平 投稿邮箱:jsune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