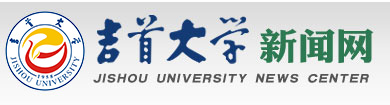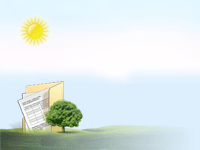图为宋旭东(左二)在颁奖现场
说实话,这里没有只言片语哪怕半个标点是我想写的,除了感谢语。在长篇小说《交叉感染》出来前,我没有认真写过小说,七年前仅有的一部中篇小说《岩泊渡》虽说获得过凤凰网首届原创文学大赛奖,再看已被我毫不留情从七万多字删减到了二万五千字仍觉失望。这就像青春时期的爱情,青涩夹杂美好,此时心,彼时情。
写小说前,我写过散文也写过少量诗歌,还写过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相较于虚构的小说私以为这些都能够更加直面现实生活,生活的混沌模糊扼杀了诗歌的灵性,散文看上去成了最后的信仰救赎。大学时期写文章,大部分是为了吃吃喝喝或作免费旅游,以及微不足道的成就,弄花掬水的手不得不捧起吃饭的碗筷。如今,可对青天白云发誓:写文章并非主要为利,热爱占大半,何况现阶段微薄的稿费我实在看不上。但我对待任何一部作品都神圣而认真,无论结局如何,只要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就一定要划上最后一个满意的句号。仿佛成为一种信仰。写作的过程对我而言是快乐的、享受的,我不希望成为稍纵即逝的快感,这快乐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将心中所想脑中所思转化为纸上文字,引导一部分人,感染一部分人,然后开启新的篇章。似乎,只要我想并为之努力,结果就能如我所愿。
人不活跃,就会死去。抵达南京南是在傍晚,和任何城市的傍晚没有两样,暮色匆匆,人潮汹涌。关于这个地名我在来时的高铁上作过百般设想,一同前来参赛的伙伴们如果各自发挥所长,集体写一部关于逃离或者聚集的小说,捎带就有拍成微电影的潜质。这超脱了获奖的意义。十年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写过一些文章,走过一些地方,到过一些国家,也经历过一些人,现实远比任何一部小说都精彩却写不出来。渐渐觉得:没有什么地方非去不可,没有什么人非见不可。这部小说我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加上后来的修改,到二零一六年足足有三年光景。从大学毕业到度过人生第一个低谷期,这部小说也从不成熟日臻完善。中途有几次都想放弃,最开始的结局要现实也要残忍的多,后来一觉醒来直接替换成了现在的结尾,原来一万多字的结尾被我尘封在了文件夹里。或许,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文学路,道艰曲折而精彩。关于创作,秘诀就两个字,一个是创,一个是作,既要练习,也要开创。练习是积累,量变,开创是升级,质变。很多人半辈子写过几十几百部作品,到头来没有一个经典。个中缘由,自行探究。大学毕业前夕,我将几十万字的修改稿装进新买的铁盆抱进公共厕所,付之一炬,来不及浇灭的浓烟从顶楼冒出,熏得大家四散而逃,终于赶在保安到来前将灰烬一骨碌冲进了下水道。同学们问我为啥烧掉书稿,我说我不想留下我珍贵的手稿。毕业后,作为一名创作者是孤独的,和银行抢劫犯差不多,要谋划布局,要结合外部环境,要分析组织策略,要保持充分耐心,要有时间概念,要有分销安排,一个步骤都不能错,既费神经也死脑细胞。
从南京博物院出来,有人正在摆摊烤五香豆腐和狼牙土豆,是一位中年大叔,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饥饿,夹了一片让我试味,豆腐和土豆我各买了一份。豆腐香不香先不说,土豆一点都不像狼牙。还没吃完,大叔拖着烧烤车飞也似的跑了,有顾客追着付钱,以为是城管,原来来了一辆大功率洒水车,尘水飞溅。
午后的梧桐叶,被阳光裁剪成金黄,点缀在马路上。沿着高低起伏的人行道走了约四十分钟,实在疲惫,坐在街边一家镶有落地窗的超市高椅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咖啡已凉,也不敢喝。到先锋书店外门口时,已经四点多,是一处众人打卡的网红书店,防空洞构造,隐约透着一股宗教信仰的意味。购买了一份“先锋盲选”,尽管旁边制成牛奶袋子一样软软的书壳包装袋更吸引我,背对一副巨大的黑色十字架上行,人影穿梭在镂空的书架里恍如迷宫。我感觉到空气不流通,有点窒息,坐在小凳子上缓和。拍照的人比看书的人多,看书的人比买书的人多,年轻人比老年人多,女人比男人多。这也是当前书店的真实现状。我不禁担忧起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后的销量。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当然,线上渠道和便捷的电子书也蕴藏无限可能。回程路上,我打开盲盒,一本北岛的诗集,一本陈传兴的《银盐热》,一本李修文的《山河袈裟》。
机缘巧合,我曾亲眼目睹过我小说里的那棵树,枝干粗大,僵而不死,是棵神树,初对视的一瞬间,如闪电霹雳,我都归因于难得的际遇。
关于这部小说的授奖词是这样的写的:小说灵活转变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娴熟切换叙事时间,从现实生活中淬炼出灵光一闪的哲思。小说具有婉郁从容的成熟文风,兼具有滋有味的烟火气和峻严深沉的思索,叙事者努力寻求超拔,并以开放式结局给读者以绵袅的余味。不知道是哪位作家的精心解读,如果能加上一句“生活式预言或现实性隐喻”就更加贴切了。我努力让一部小说看起来不那么像一部小说,也努力让这部小说里面的主人公看起来不像是主人公,甚至是无名无姓,姓名只是一种肤浅的符号,何况大部分人记不住。言语对白代替曲折传统的故事叙事,我也想方设法寻求一种结构上的转变与创新。而这些,又何其艰难。
写这篇文章时,我刚修改好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某个章节,小说的出版或将让我更加有信心写好接下来的作品。颁奖礼上,苏童说,要想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耐心和持久度是关键。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作品完成后的反响程度,要么期待获奖,要么期待畅销,长此以往,很多作家难免产生焦虑的心绪,这对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是极为不利的。最近,晚上老做梦,回环往复的想《漫长的告别》这部作品的名字,越想越觉得这个翻译过来的题目真是好,为啥我就没有想出来,再一看,雷蒙德·钱德勒几十年前就想出来了。这和一名作家想耗费毕生心血创作出一部流芳百世的作品一样,可遇不可求,唯有坚持下去才能有朝一日下个路口见。
生活的无所适从,价值角色的错位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不能再走传统老路,不能再拾人牙慧,更不能闭门造车,要争取创造一点新的东西出来,哪怕前期不成熟,也能发出愈久弥新的光芒。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我会一直坚持写下去,下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我也坚信,伟大的作品正在前方等我,时间和空间会为我佐证,每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终将会实至名归。
我从椅子上下来。稍微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
回想我的写作生涯,大部分文稿都是在餐桌上写的,到现在都没有个完整的书桌,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考虑忽略了自己读书人的位置。当然,在哪里写不重要,能写成什么样才是最重要的。有人说我写的真实如同亲身经历,我说我这个年纪哪能经历那么多诡谲美好的故事无非是别人的故事借我的口吻说出来而已,再就是形形色色的电影题材都是宝贵的灵感来源。但如果缺点天赋又是无法进行二次创作的。想象力和持续的生命力是创作的源泉。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喷发,比为了写而写永远要高明。
翻翻七年前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赫尔德瓦尔的河》,是青春,是成长,是记忆,是支持也是感恩。看看后记,我写了很长很长的话,也感谢了很多人,有些人已经离开,有些人依然在,这些都是人生不可多得的际遇。这部小说的完成地是在长沙,是我成长的地方,也是我曾工作的地方,还是我完成人生阶段目标的地方。顺着该部小说的创作轨迹,添上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感谢父母家人陪伴支持,感谢母校吉首大学书记校长等领导关心支持,感谢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书记院长等领导支持厚爱,谨就此书,感谢所有默默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人生之路,每个人都算数,希望今后的人生也能与大家一同前行。
最后,谨向全力以赴将我培养成为一名真正作家(或与之相近者)的《青春》杂志社、出版社(江苏出版传媒集团等)、各位责辑,献上我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是为后记。
(责任编辑:苏卫平 投稿邮箱:jsune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