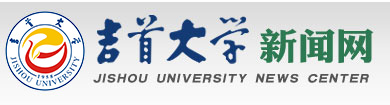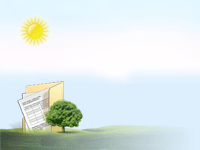罗叔今年49,人不高,有点黑黑的,笑起来总是很腼腆。
按辈分,叫叔其实不合适。罗叔是我老舅公的儿子,是外婆家乡衡山罗家村的直系亲属,只是在村里时大家都这么叫,一来二去,也就惯了。
我一向不喜欢去衡山,无论拜年抑或访亲,一是难走,二是无聊,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主义的思维定式。
记得上次来罗家村还是去年春节例常的拜年。坐了大半光景的车子,山路崎岖不平,二十公里的路程趑趄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这一次还好,只是再度站在村口庙观的大门前,心里无限失落,我是和家人代表奶奶来参加老舅公的白喜事的。
前些日子因为疫情封了路,葬礼早已结束。村里静了许多。
才下车,远处就走来一位瘦弱的中年人,近了,才发现是罗叔,这月份山里冷得人直哆嗦,他却只是穿件单衣、披张粗布马褂、戴着顶破翻毛毡帽,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看见我们,罗叔愣了一下神,听见我们向他打招呼后,脸上立马洋溢起微笑,一路小跑着去叫别的亲戚。
罗叔还是老样子,只是感觉比记忆中的更矮了一点,黑了一点。在罗家村,同他作伴的基本都是老人,从三舅公到老舅公一共三户亲戚,其间和罗叔莫约一辈的人都选择了外出务工,仅留下他一人在附近烟花厂工作,同时照顾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父母和村里其他亲戚。
才把东西放下,罗叔便急忙关切我们要不要喝点热水,还未来得及听得我们答应一声,罗叔又马不停蹄走开了。他习惯擦着地板走路,宽大的裤子风一吹就鼓了起来,总叫我想到茕茕孑立这个词。罗叔转身走进了厨房,把水壶提出来,一边给我们和陆续进屋的老人们倒水,一边念叨:“天气冷,一定要多喝点热水暖暖身子!”挨个伺候完,他坐下来,点根烟,开始听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论近况,偶尔插上两句,又缩回椅子听大家说。
情绪最激动的是一旁的二舅公,我看着这个满脸褐色斑纹、头发稀疏的老人家,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二舅公把原本戴在头上的帽子摘了攥在手里,挥动着溢于言表的愤懑——该死的疫情子女都回不来了,老舅走路摔了一跤脑溢血了……情不自禁处又忍不住用黝黑皴裂的手指擦拭滚下的浊泪。“老一个就少一个”,他说。穷山恶水,村里的老人身体都不好。算起来——二舅公丧偶也有好些年了。
我下意识偷偷望向罗叔,却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悲哀,只是愈发不响,独自出了门。回来时罗叔手里多了把沾着泥土的野葱。他闷声走进厨房,不过一会,小屋子里飘出炒菜的香味,原来是忙着给我们做饭去了。
母亲示意我和表弟进厨房,问问罗叔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罗叔看见我们连忙摆手,吩咐我们随便坐着就好。他在电磁炉上做野山葱炒肉,闻起来很香,只是葱和肉都切得过大了,看起来就像角落里胡乱砍断的树枝和破叶,有些滑稽。我想提醒他,但转瞬又打消了念头,无奈杵在一旁默默地观望。罗叔撒了一大把味精,屋外的小黑狗闻见香气小跑着进来,却也只是趴在罗叔的脚边,有那么一刻钟小屋里的一切都显得过于沉静。
我记得往年没有电磁炉,问他为什么不烧柴火、用灶台和大铁锅做饭,他说村里老人四点就吃完了,给我们做用电磁炉就够了,新买没多久的。说罢又从壁橱捧出一小篮鸡蛋,说我给你们再煎几个荷包蛋吧,院子里的母鸡又下了好多蛋,我都在这留着。
那些鸡蛋没来得及洗干净,蛋壳上沾着些碎稻谷与淤泥,些许腥臭。我摇摇头,不去想关于菜的事情,而是尝试找话题关心罗叔的事体。罗叔都快到知天命的岁数了,还没有结婚。说起早年下山的经历,他摇摇头,说自己或许还是更喜欢山里。他望着沸腾的电磁炉发了呆,那几簇早先特意洒进去的香麻油全都被锅底翻涌升腾的气泡赶到了锅边,白雾顷刻氤氲,看不清他的表情。
做好了菜,罗叔去壁橱找了两副碗筷,让我们快些吃,自己又忙着出去了。再进来,抱着一堆柴火,在桌旁生起一个火盆。他用温和柔软的乡音低声说,你们吃完来烤火呀,天气冷。
山中的时间似乎流淌得很慢,和托马斯曼的《魔山》一样,几个老人次第远去,没有往年那般热闹的酒局与闲谈。我咀嚼着咸齁的腊肉块,思索新年依稀的余味,还是有些索然。可能人越长大越多心绪,罗家村虽然偏僻难走,但其实偶尔来和长辈亲戚们聚聚、围炉夜话,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只是现在年华一帧一帧地老去,我觉察一切尽头的乏味。也不知道罗叔心里,是不是同我一般困惑着。
饭后才五点多。山中的风逐渐放肆吹开,亲戚们便各自回屋了。我想起几天前才抬上山的老舅,心里很想去拜一拜,刚好表弟也提议——我们去山间走一走吧。两个人装了几束香和纸钱便走了。
虽然已是仲春,山里还是凛冬的模样,暗赭的残叶把山路铺出厚厚一层。冬天过于尖锐,许多树的心胸变得狭隘,许多许多的鸟儿飞走了。我踏上小径,有清脆的声音,在静若太古的山中格外清晰,走着走着,仿佛传来沧浪水声,又疑是林海追风,便驻足谛听良久。那席卷而来的山风啊,所到之处都像掀起阵阵巨浪,想起《海滨墓园》的绯句,“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心底更是泛起一阵难名的酸楚。
我们留意着山里新立的坟冢,每一座都上前仔细查看墓铭,可都没有看到老舅的那一座。直到看见两座并在一起的无名坟冢——一座有点老,一座看上去就是新土才建的,站在墓前,我突然萌生强烈的预感,这应该就是老舅的归处。旁边,应该是老舅母的,看着老舅母的坟墓,我甚至感觉,自己已经来过。
暮色四合,落日余晖把远空染成温柔的粉黛,月亮挂在稀疏的枝桠间。坟冢旁边还散落着一些纸钱和青香,想象老舅生前的模样,那位骨瘦嶙峋热爱写字的爷爷,他就躺在这片土地下面。周遭的松木被林风吹得像山泉一样哗啦啦地响,从每一个毛孔浸润我的四肢百骸,我突然觉察出一种深深的恍惚,似乎都是在梦中,罗家村的某一间小土屋里,平素喜欢戴着老花镜背着手的老舅,他应该还伏在桌前练书法。
我忆起《寻梦幻游记》中一句台词,“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起初,村里老一辈亲戚去世,都会安排砌水泥墓、立石碑,村里人越来越少,子女相对富足的老人也被陆续接往城中,山里就仅剩下几位了。再有老人去世,好像就是匆匆几抔黄土。那些小小的不起眼的坟冢看似紧紧相依,实则彼此孤立无援。有时候,记得本身就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情。再过五年、十年,或许这个村庄就不复存在,彻底消失了。这声遗憾叹息来得会比任何季节都要悄然无声。到那时,罗叔一个人,又该怎么办?
第二天我去了老舅的屋前,门边的挂历还停留在2月9日,那是老舅被抬上山的第二天,日历就再没人去撕过。门上只是虚扣着一把锁,两旁新春的对联上写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中午隔壁的三舅母拿了一碗油炸豆腐给罗叔,让他每顿给我们加点餐。心情好的时候,罗叔做菜会唱歌。我悄悄拿了手机准备录下来,罗叔看见后摸着后脑勺腼腆地笑着说他不好意思唱了,我说没关系,你就当我不存在。即便这样说,罗叔还是郑重其事地看向镜头,小声地唱了起来,“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你心中苦与乐”。
午后罗叔带我们去田野里,三舅母在种山药种子,他在旁边插木桩,说来年藤蔓就爬上去了,到时候可以刨点山药给我们。罗叔开始自顾自说起山里的趣事,说公厕旁边铁笼里的大黄狗,腿其实是残疾的,因为它小的时候跑到山里玩,被废弃的狩猎夹夹到腿,腿就断了,还说起梨树、枣树、珍珠李节令细微的差别,夏天或者秋天来,这边水果就多了,到时候,一人给你们准备一大包水果回去慢慢吃。不过,你们以后会不会来不一定了……我没有听进去太多,只是觉得天愈发冻人了。表弟在一旁悄悄问我,如果让你在这里呆一辈子,你呆的下去吗?我想了好久说,不知道。
由于家里有事情,提前吃过晚饭就得下山。
罗叔给我们每个人煎了两个荷包蛋,还油炸了豆腐皮、煮了山里新鲜的白菜,做了瘦肉汤,让我们一定要吃完。塌耳朵的小黑狗目光如炬地看着我,我悄悄把碗里的肉丁丢给了它。
罗叔的大锅里煮着我们之前买的汤圆,他说既然你们就要走了,那一会儿你们和爷爷奶奶们一起吃,也算是和他们一起过节。
我一碗一碗给老人们盛着汤圆,他们一声一声感谢着,挽留着,那位耳背的三舅公大声地说,别走了嘛,今晚还要一起过节呢嘛!
我并不太饿,只给自己盛了几个,剩下十余个打算留给老人们。罗叔立马制止,难道你不吃了吗?陪爷爷奶奶过节,你也得吃啊!他给我的碗里舀了五只大汤圆和两大勺白糖,说甜甜蜜蜜地再吃一碗,才算过节。两勺白糖和进去,汤汁立马浓稠起来,吃到最后都没有完全融化,罗叔看我们都吃完了汤圆,紧皱的眉头才得以舒展。
那天走出罗家村的时候,罗叔执意要帮我们拿行李,其实都只是些轻便的衣物。他一路都没说话,表情有些严肃。耳朵有点背的爷爷也从自己小屋子走出来,他笑着挥手,听不清我们的嘱咐,却自顾不停说着些道别的话......
回到城中,天色已经很晚。我裹着去年的棉衣靠在沙发上,盯着电视机的屏幕出神。画面里是元宵晚会重播循环,锣鼓喧天响彻云霄。可我只是想着罗家村的人们,二舅公的眼泪、三舅母的蔬菜、罗叔务工的烟花厂,和他那点微薄的补贴......烟花与鞭炮已经随法规禁绝了,近年没有噼里啪啦的动静来恼人。间或几处不知名的角落虚张声势地响起,不多时,也就偃旗息鼓。世界又重新陷入了一片歌吹中。
我对一旁的表弟说,今年的晚会挺好看的。表弟努着嘴一个劲摇头,反驳我哪好看了?不还是老样子。我答不出,一时有些局促。可能也说不上好看,但是是老样子,这也就足够,我想。就像那鞭炮声——听久了,心里难免厌烦,但是明文禁绝后,我反倒思索起它存在过的证明与意义,要兀自怀念起来。
马齿徒增,只教我学会了贪恋这粗俗的热闹。
我蓦地想起前日听罗叔唱歌时他悄悄和我说过的话。他说他感觉自己老了,老舅去世了,自己也不剩多少年啦。那时我假装生气,叫他不要胡思乱想,安慰他“好人一生平安”。
可是罗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老了。
每当夜色沉沉的时候。
(责任编辑:苏卫平 投稿邮箱:jsune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