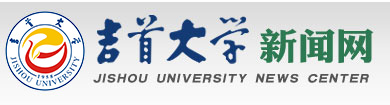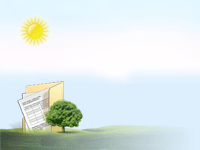父亲护我是有名的。三姊妹中,从小到大,只有我从没挨过父亲的骂,甚至一句重话也没有,更不用说挨打。那时侯和我妹吵架,被骂的总是我妹。她就以哭抗议,“爸就是护你!” 很多年后,和我妹说到小时候的那些事,我妹仍然免不了要强调一句,“爸就是护你!”我也一直以为爸是护我的,不管我做得如何。
但我的脾气好象并没有被宠坏,我不但是这个小家庭中三姊妹的“大姐”,还是我外婆那一大家子同辈孩子们中的“大姐”(我外婆一口气生下十一个孩子,这样,我就有三个舅舅7个姨,他们又生下了一共30个左右的孩子)。在我这一辈一起长大的孩子中,我是极懂事的,从小就得到长辈们的信任,一点也不象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大了,倒愈象是个孩子,不懂事了。很多事不明白。是不明白这个社会。我爸说,别考博了,不吃那苦,让你妹去考。现在我妹博士后毕业了,而我,成了吉首大学最年轻的本科生。这是后话。
那时没事就给我爸捶背。站在他身后,边捶边说,爸,给我讲个“唉作伙”的故事咯。其实我已经听过八遍了,我闭起眼睛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似乎并不在意父亲讲了什么,而是在意父亲在讲,而我,漫不经心地在听。父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每次讲都会有一点点不同,让我得到一点点新奇。而我每次都会得笑得前呼后仰。完了我会把它原封不动地讲给我妹和我弟听。他们也至少听过八遍了,但也象我一样笑得一塌糊涂。生活简单得要死,我们却极其享受。
那时候我屋里养得有鸡有狗有猪,还在茶叶队分的三分半菜地,很多往事,都与这些东西有关。我一样样说。
我从小就喜欢种菜,我家的菜地,大多是我爸带着我去打理。我甩开两手走在前面,我爸挑一担粪跟在后面。这种记忆非常深刻。初春的气息湿润清爽,清明的鸟儿在斗上叫着,我问父亲,它们在叫什么,父亲说,它们在叫“清明酒醉,腊肉有味。”然后他就学那鸟儿的叫,打起呼哨,悠悠脆脆的声音在空中飘了起来:清明酒醉,腊肉有味——
父亲挖地的时候,我就把那些大一些的石头从挖松的土里挑出来扔掉。有时候会挖出一些蚯蚓和不知名的小虫子,我一手抓起来,向父亲炫耀“爸,你看!” 我从小就不曾怕过地里的什么小虫子。把它们抓起来又重新放回地里。
对于地里该种什么,我并不知道。但不拘我建议什么,父亲都是笑呵呵地同意。而末了父亲是不是照我的建议去做,我却从不关心。我说,爸,我们在这里种黄瓜,种这么多,长得比人还高!父亲说,好!我说,这里呢,就种韭菜,一蓬一蓬,炒鸭蛋吃,我最喜欢吃了!父亲说,好!还有这里,我跳到另一处稍远的地方,这里就种苦瓜!你喜欢吃苦瓜,就满足你的心愿!父亲说,好!到后究竟种了些什么我却不在意了,往往是父亲早就有所准备,把带来的种子撒进去,我就用薄薄的一层土把它们盖上。
我喜欢看种子发芽的样子,绒绒的,嫩嫩的,破土而出的样子。我掐着手指算,对父亲说,爸,都有十一天了!种子该长出来了吧?然后不断地央求父亲带我去看看。最终,父亲都会同意我的请求,我们便一前一后地上路了。
那时候我们家种的菜吃不完。屋里堆满了我们从地里收获回来的南瓜、东瓜、葫芦瓜,码好高,齐屋顶了,还有包谷、茄子、西红柿,豆角、白菜等。有的被做成了酸菜和干菜。我现在记不清它们的季节了,反正是天天有吃,从没厌过。我还曾带我妹上街卖白菜。摆在马路边,混在一群卖菜的妇女中间。白菜摆好了,却又胆怯了。第一次卖菜,怕丑。好像是小学三年级。但那卖菜的心情却实实在在记下了。在想,下雨吧,这样我就可以把伞撑开,心安理得躲在伞后面。别人问,白菜好多就钱一斤?我就躲在伞后回答,白菜两分钱一斤!雨硬是没下,躲在伞后面不成。看看周围的人并没有注意自己的,就渐渐地放大胆子,神色也渐渐自然了。我和我妹轮流吆喝起来,白菜,白菜,两分钱一斤!卖了多少白菜已经忘了。但我从种菜卖菜中得到快乐,却是真实的。我天生是个菜农。
有一个夏天,我和父亲从地里回来,从古阳河大桥下过,就在桥墩下歇凉。蝉儿在远处叽呀叽呀地叫着,天空蔚蓝。父亲洗完了脚,在河边抽烟。我看见虾子一群群在水里,密麻麻的,就对父亲说,爸,我们撮一盆子虾子转屋炒吃!父亲说,好!我把筲箕里的菜摆在河滩上,用筲箕开始撮虾。这个愉快的下午,我满脑壳是流动的水和虾子。湛蓝的天空倒映在水里,刚刚一会儿平静,忽又很快被一群游来的虾打乱。而我,追踪着虾群,一身的衣服浇湿。父亲在旁边等着,不骂,也不催。直到夕阳西下,我肚子咕咕叫了,才回去。临行时,我看着盆子里的虾子,它们虽然挤作一坨,仍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完全不知道可能等待它们的命运。我对父亲说,我们把虾子放了吧,父亲说,好! 我把虾子放回河里,便和父亲,一前一后地回家了。
父亲一直很坚强,即使在生病期间。他使劲地多吃东西,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还不断地安慰我们,说些医院的趣事。我们在医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我甚至没有把他当成病人。我希望有奇迹发生。直到那一天,当我给父亲说着学校里的一件事时,我以为他会象往常一样和我一样高兴,但是他突然茫然地问了我一句:“你在说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猛然觉得我爸不行了,爸的意识已经无法控制他的身体了,病魔正在一点点带走他。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无比的悲凉,我爸真的要离开我了。
父亲走了,没有人护我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天在灵堂里,父亲躺在灵柩里面已经两天。我用力掀开搁在灵柩上的盖子,我还想看看我的父亲。他明显地瘦了小了,象被抽干了水分一样,面色苍白。我摸摸父亲的手,僵硬的,象石头一样冰凉,使劲摇也摇不动。我的泪水飞溅而出,一遍遍说,爸,你起来,给我讲个“唉作伙”的故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