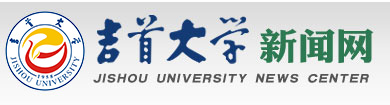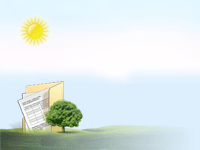每年深秋,母亲总能最先在寒风中嗅出甘蔗成熟的气息。天蒙蒙亮,母亲就站在院子里,等甘蔗农进城,从他身后的板车上拣几根深秋的味道。因为母亲,我家每年都比别人先吃上新鲜甜嫩的甘蔗。
甘蔗买回来,母亲用刨子从上而下细细脱去甘蔗青绿的外衣,露出光滑如玉的嫩肉。她把甘蔗砍成几小块,避开了硬邦邦的关节,把易咬的部分盛在碗里,端给我吃。我吃得又急又糙,一通乱啃乱嚼,母亲坐在一旁,从地上拾起浪费掉的蔗渣,塞进嘴里,蚕食桑叶般,密密地咀嚼着。她喃喃道:“每一丝甜都来之不易啊。”
母亲对甜味的记忆都停在一九七五年。那时,她刚刚十六岁。安徽老家大旱,处处闹饥荒。外婆为了让孩子们多扒饭填肚子,炒菜时总狠狠洒两勺盐。墙角摆着的咸菜坛上积满厚厚的灰,像饱经风霜的老者,用浑浊的眼孕育这个贫穷的乡村。人们吃的菜是咸的,淌的汗是咸的,连流的泪都是咸的,整个人都是盐巴做的。
饥荒熬过去,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大地终于重新喘气,甘蔗地渐渐漫着碧波,人们的心也跟着饱满膨胀。
几场秋雨后,母亲驮着一把铁锹和外婆下地了。甘蔗挺得笔直,锯齿状的叶子割着来往的秋风。甘蔗是顶着霜冻一寸一寸拔生出来的,关节处还深深留着淤青,茎杆处爬满锈红、泥黑色的伤疤。母亲用手握住比她的小臂粗了一圈的甘蔗,铁锹一落,清脆一声,甘蔗倒伏下去,叶子临空乱晃一阵,身子匍匐在地上,以取暖的姿势紧紧蹭在一起。铲了几排后,母亲的旧布衫染满了绿色的汁液,大腿、手臂、手掌添上无数道细小的划痕,也像层甘蔗皮。累了,母亲就坐在一堆胡七乱八的甘蔗叶上,拦腰掰下一节甘蔗,捋去叶子,牙齿像榫卯用力咬合,甜丝丝的汁水撒欢地跑进胃肠,味蕾一个个都活起来了。母亲是每年最早尝到甜味儿的人。
婚后,母亲跟着父亲到城里,日子依然凄惶。白天,母亲既要打几份工,又要照顾我。她像装了电动小马达,一直在家和厂里来回奔波。即便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她也毫不吝啬我的吃食,常给我买糖水冰棍、糖炒板栗、甜瓜,自己吃咸菜喝粥。
只有到了深秋,母亲才会有一段短暂而美妙的时光。她请假回乡下,帮外婆收拾甘蔗,陪她唠嗑。回来时,十几根甘蔗被牢牢捆在自行车后座上,上下震动,像翅膀。母亲一路披着金色的阳光,踩着脚踏,嘴里哼着梅兰芳。直到外婆去世,母亲才彻底断了与甘蔗地的缘。
零六年,母亲兴冲冲地提回那年秋天的第一袋甘蔗回家。我们一边晒太阳,一边啃甘蔗。只听“咔”一声脆响,母亲把手伸进嘴里捣鼓一阵,掌心竟躺着一颗米粒般的牙,白嫩的甘蔗一片猩红。她痛得直撅嘴,眼睛却是笑着的,很无所谓的样子。她支起身子,慢慢踱到房间,用手绢把牙齿包了几层,佝偻的背影在我眼前缓缓晃动,渐渐模糊成一条线。
母亲掉了一颗牙后,其他牙齿懒怠不少,终日摇摇晃晃,大有罢工之意。没有了牙,母亲就把甘蔗削成小小块,拿牙床慢慢地磨呀磨,瘪瘪的唇紧紧含着甘蔗,像一台密密绣花的缝纫机,亲密得没有距离。磨了会儿,舔舔嘴唇,回味半晌,吐出蔗渣,捏捏尚有水分,便又塞进嘴里,温吞水似的左右嚅嗫,反反复复,甜蜜极了。
我心生不忍,在网上买了几罐甘蔗糖,可用来泡水喝。母亲喝了几次,就再没有见她开过盖子。我才懂得,母亲并不是贪图那舌齿之欢,而是爱从甘蔗里细细咀嚼出生活甘甜,爱那抹不管陷进多大的泥淖,也要让生命拔出腿来,树立在寒风中的翠绿。就连满地的蔗渣她也爱,她把它们扫在树下,留做日子的养分。
母亲过了六十岁,身子常常感到冷,半点凉食都吃不得,就连甘蔗也不能沾了。她坐在凳子上,眼神飘忽,一会儿低头看掌心,一会儿看远处昏黄夕阳。
“卖甘蔗咯!”愈来愈近的哟呵声里,母亲的目光亮了。
(责任编辑:见闻 投稿邮箱:jsuen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