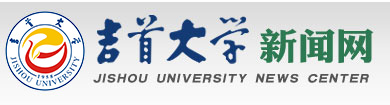我右手的食指上凸起一块约半厘米高的厚茧,像广阔无垠的平原上贸然隆起的小山丘,显得无比格格不入。
这块醒目的厚茧,正是因我长年累月拿笔姿势错误而磨起的笔茧。当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我无数次告诫、强迫自己换用正确的握笔姿势,无奈习惯猛如虎,多次苦苦追求却无果而终,我灰头土脸地高举白旗,被迫采取放任政策,任其如野草一般恣意猛长。
上初中后,我痴迷上写作。少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有“一窗昏晓送流年”的如火热情,有“闲看中庭栀子花”的潇洒烂漫,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美妙绝伦。一个个鲜活恣肆的文字在我笔下开出水灵灵的莲花。其间笔茧不离不弃,不懈努力,终于显山露水地占据了一方领地。看其张牙舞爪、爽爽有神的样子真是可恶至极!就像一幅绝美的山水画上豁然现出一败笔,使整张画卷黯然失色。由于其相貌十分丑陋,我日常与朋友相处时总是藏藏掖掖,不让它轻易见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这种笔茧是完全可以动手术切除的,大为窃喜,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清亮欢快之感。我怒视老茧在心里恶狠狠地说,等我上了大学一定将你大卸八块,与你血肉分离,来扯断我们十几年间缠绵悱恻的纠缠。
后来上了高中,我常常做习题到深夜。阒寂的夜晚,月浅灯深,凉薄的灯火将我疲惫的思绪温柔簇拥,分外孤单。这时家人已然酣睡,惟有笔茧仍默默尾随我,像我忠实的战友,与我共进退。我用力甩甩发酸的右手,不经意间瞥到我的“老战友”因为长时间被笔杆重压变成了骇人的血红色,就像刚刚喷发的火山,四周漫溢着火红色的岩浆。看着笔茧饱受摧残却宁死不屈、昂首挺胸的样子,我不禁有些同情与敬佩它。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与笔茧时而惺惺相惜,时而硝烟四起,一起走过一年四季。这样动乱不安的日子直到我读到冯骥才的一篇散文时才终于谢幕。冯骥才那段自我剖析着实让我记忆犹新并为之震撼。他回忆,他一生说不出有什么大作为可以不朽,只有书桌下的水泥地因他几十年不舍昼夜地伏案写作而被踏出两个浅浅的坑,证明他存在的价值,让他在面对天王像的诘问时安若泰山。这一席灵秀文字如醍醐灌顶,让我幡然醒悟。我意味深长地端视我的笔茧,顿时感慨万千。毋庸置疑,我的笔茧不也正是我笔耕不缀的结晶、青春飞扬的旁证吗?它像一座闪亮的灯塔矗立在知识的海洋上,并不因相貌丑陋而怪诞使人远离,如同维纳斯女神的断臂,因残缺不全而神秘广为流传。凸出的笔茧,其实是标新立异的旗杆,是一种极致的情调。
笔茧依旧与日同增,而我却感到无比的愉悦,在往后的日子里会更加珍惜它。笔茧呀,我将以持之以恒的奋斗来维持你我之间的永久情缘!
(责任编辑:苏卫平 投稿邮箱:jsune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