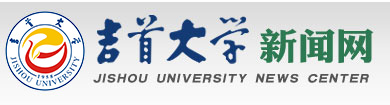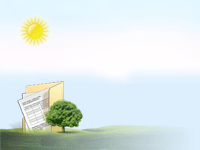我和易校长的相遇相知,是在1980年暑假。那时我在大庸县一中任教。大约是五六月份,延安大学发来商调函,邀我去任教。我自1959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在甘肃定西师专等校任教,其间还被保送到甘肃师大(现在的西北师大)中文系进修了一年,1976年年底调回湘西大庸县。改革开放后,全国高校到处缺人,所以延大才急急发来商调函。这一下可惊动了州教育局,赶紧下文将我调至州教师进修学院。
7月下旬,吉大派程功和部长和王国干同志,带着商调函到大庸县教育局商洽调我之事。但州局的调令在先,此事无法商量。程部长便给我出主意,叫我亲自到吉大找易校长面谈。易校长见了我,问我在大学的主攻方向,在师专教什么课,在甘肃师大进修什么课,还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经历。我一一作了回答。我们交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易校长便说,我们欢迎你来吉大任教。
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于1981年8月调入吉大中文系,一直干到1999年12月25日退休。其间20年,我开设了四门课,出版学术专著、长篇纪实小说、诗集、文集五部,主编合编书八本,共计130余万字。论著及文学作品获国家级奖和省级奖各三个。1995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这点小小的成绩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如果没有老校长接纳我,没有吉大这个平台,让我在中学“混”一辈子,我想自己恐怕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拿不出来。
老校长是一个真正的学人,经常“微服”听课。我有几次上课,讲到中途,突然发现老校长坐在凝神听课的学生中!我当时正在手舞足蹈,激情洋溢地分析一篇文学作品呢,赶紧收敛起来,严肃平静地往下讲。下课后,我征求他的意见:我这么讲行么?他说行,但不要这么细,还可以放开点。我知道他此说的意思是,不要像讲中学语文那样窄和死,应当注重意境的开阔,韵味的深长,高瞻远瞩,如天马行空,如放风筝,纵横捭阖,能放能收,尽量开掘作品的艺术内涵,尽量让学生融进去,充分感受作品所营造的潜在艺术空间与氛围,以便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力、想像力和创造力。他是解放前老湖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当助教,专攻古典文学,古文功力深厚。在他面前,我是心甘情愿当他的小学生的。
大概是1984年的5月份吧,有一天易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现在对写作课有什么想法?是不是还想改行?因为我在大学读书时是专攻文艺理论的,到定西师专后又准备过苏联文学,所以进吉大之前,易校长曾答应过让我教文艺理论。后来写作课缺老师,才叫我暂时顶上,以后有机会再改。我听到易校长提起此事,心里特别感动。我很激动,也很真诚地回答他:易校长,我觉得教写作挺好的。别人说,教写作不容易出成果,但我觉得我教写作能出成果,所以我不想改行了。他说,很好。现在准备叫你来担任写作教研室主任,怎么样?我一听,哦了一声,深思了片刻回答说,易校长,此事让我考虑一下再回答你,好么?他说可以,给你两天考虑的时间。我见他这样信任我,器重我,又能这样民主地对待我,我被感动得差点涕泪双流,不敢有半点敷衍。第二天我去向易校长表态,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并保证干好。易校长听后也很高兴,并鼓励了我几句。
易校长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1985年 上 学期,易校长挑选我和龙长顺作为中文系重点培养对象。命科研科谷科长,让我和龙各选出几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自己选定专家教授,由科研科寄出,请他们进行鉴定,为评副教授提前作好准备。我和龙老师各选了五篇论文交给谷科长。我选定的鉴定人是全国闻名的文艺理论家,也是我的老师陈涌先生。他是中国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他的鉴定评语非常严肃尖锐,优点缺点一并指出,但他对我的论文总体评价还是较高的。其中有一篇《试论“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的理论及实践根据》,获湖南省教委“六五”期间科研成果奖。但是到了1986年下学期,学校评第一批副教授时,我没有入选,当时心里有点不服气。10月份左右,我到湖南师大开会,正好易校长也在长沙的家里休假。我便抽空跑到他家里向他打听,这次评副高有没有我。他坦率地告诉我,你任讲师的时间只有三年,按条例规定不能评副高,等下一次吧。我国因各种原因,有30多年没有评职称了,欠下的债太多,一时还不清啊!要体谅国家的难处,相信组织,只要自身条件过硬,该评副高、正高的人,都会在近几年评上的。
还有一件事,也叫我永世难忘。那是1983年寒假,春节刚过,老伴突然发病,经州医院诊断,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学校只得派车,由周医师和我将老伴送至永顺医院治疗。我当时膝下有二儿一女(小儿还寄养在平江县外婆家),大儿15岁,二儿12岁,女儿10岁。三只小鸟,嗷嗷待哺。一日三餐,洗衣做饭,叠被铺床,哪样事都要我一人亲自操作。我要备课教课,批改作业,还要补习外语(评讲师),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的编写工作(老龙为了照顾我,给了我写半章的任务)。我是人,而不是机器,忙得过来么?支撑得住么?我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给细英的亲人写信,向他们求援。细英的大弟弟带着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和二弟,于3月中旬赶到吉大。第二天,由内侄女照管三个孩子的起居上学、穿衣吃饭等家务,我偕两个内弟直奔永顺医院。一见到细英,我失声痛哭起来。这哪是医院啊,简直和关犯人的牢笼没有什么区别!细英因服药过量,加上惊吓,浑身发抖,整夜睡不着觉。我立即决定让她出院,由两个内弟带着她回平江娘家休养一段时间。
我一人返回吉大后,内心矛盾重重,愧疚地向易校长呈上要求调动工作的报告。我想找个就近家乡的高校教书,细英害病也好找个亲人来照顾,也免得岳父岳母挂念。我正在谋划个人的计划时,易校长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我写给他的报告递给我,只说了一句话:“你不能走!”我一听这话,如雷轰顶,震惊、痛苦、愧疚等思绪一齐涌上心头,不知如何回答。只感到老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收留下我,给了我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我到吉大屁股还没有坐热,没有做出任何成绩,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急匆匆向他提出辞呈,要求调动工作,这是人做的事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才低着头小声说道:我的孩子又多又小,细英害了这个病,叫我怎么办啊?
等她病好了,给她换个工作。教小学太辛苦,让她到资料室当资料员去吧。你心理上的压力不要太大了,放坚强些,车到山前自有路。老校长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支招,鼓励我渡过难关。我被感动得热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挺直身体,以立正的姿式向老校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再不要求调动工作了,我死也要死在吉大。”
1983年6月中旬,细英在家乡休养了不到三个月,病情基本好转。回到吉大,又休养了两个半月,新学年开始了。老校长又把我叫过去,询问细英的病情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换个工作?我回答说,她说她教了 20年中小学,觉得挺好的。她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不想改行。她舍不得她的专业啊。
老 校 长 一听,高兴地说,好吧,还是不要违背她的心愿。不过,你今后要多照顾她一点,让她快些彻底恢复健康。
我说,谢谢易校长,我记住了,一定做到。
在我 51年工龄的人生阅历中,我很庆幸能够遇到易校长,得到他的关怀、照顾和帮助。因此,我在夜深人静,或一人独处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想到他的为人和人品,想到他对我的知遇之恩。
1993年 暑假,我到厦门大学参加全国高校影视文学研讨会去了。有一天,陈焕然老师领着易校长 (那时他已是71岁的高龄,早已离休,住在长沙)来到我住的13栋楼房,向我老伴打听我的情况。老伴告诉他,我去厦大开会去了。老校长听后,才没有进我家的门。
我回来听老伴说起这件事,感到十分遗憾。自从老校长离休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1998年和2008年两次校庆,我都没有遇见他。我自2000年4月8日移居上海后,到2017年10月3日才返回吉大。这段时间,更没有机会获得有关他的信息。直到2016年4月,欧阳处长领着两位同志到上海来慰问我们时,我才得知老校长已去世,享年94岁。我当时感到很沉痛,很愧疚。他在世时,给了我这么多关怀和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可我给了他什么回报呢?没有啊!我连自己出版的著作都没有送他一本,实在不应该啊!我惭愧,我忏悔!我只能用笔写了上面一些话,聊表我对老校长感念之思,忏悔之情。
愿老校长在天之灵安息吧!
(责任编辑:苏卫平 投稿邮箱:jsunews@163.com)